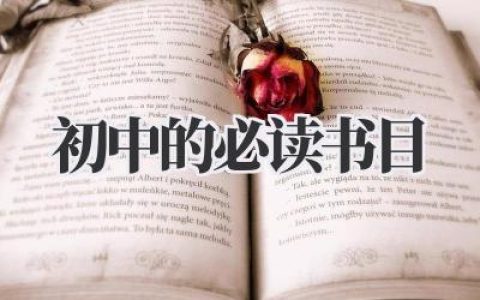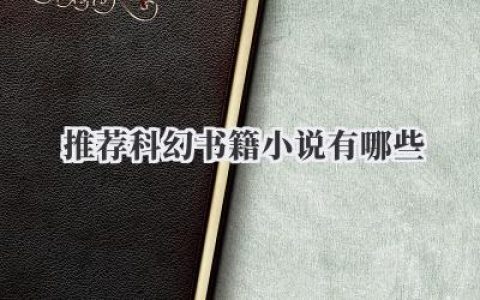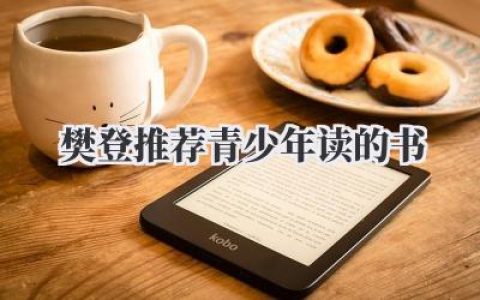他曾苦口婆心地劝青年人,多读外国文学,尤其是俄国。那不是因为俄国小说里有“好听”的情话,而是那里有血肉淋漓的挣扎,有灵魂深处的拷问。你读屠格涅夫的《父与子》,会听到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噼啪声响,那是时代的车轮碾过人心。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,那种罪恶感与救赎的纠缠,人物内心深渊的呓语与嘶吼,绝不是“好听”,而是令人心悸、令人窒息的沉重。可正是这份沉重,敲打着你的神经,逼迫你直面人性的幽暗与光明,读完,却仿佛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洗礼,余音不绝。这种“好听”,是醍醐灌顶的痛感,是震耳欲聋的警钟。
再看他推崇的那些古籍。他自己就曾沉浸在《史记》的浩瀚里。那不是一段段枯燥的史料,那是人物的呼吸,是命运的叹息,是权谋的低语。你读《项羽本纪》,听到项羽乌江自刎前的悲歌,那是一代霸王英雄末路的绝唱,是历史洪流中个人悲剧的铿锵回响。读《报任安书》,司马迁那种隐忍不发、字字泣血的悲愤与坚韧,穿透千年,依旧能让人心潮澎湃。这岂止是“好听”?这是历史的交响,是命运的合唱,它将你带入古人的世界,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,在宏大的叙事中寻觅个体存在的意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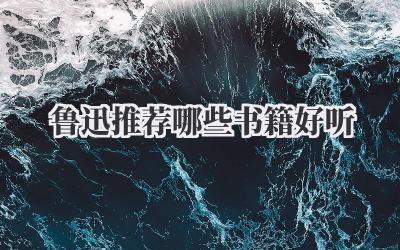
还有《聊斋志异》。鲁迅先生对其的评价是“用传奇法,而以志怪。” 听起来,是带着些许神秘与妖冶的调子。那里面的狐仙鬼魅,与其说是妖,不如说是人。它们的故事,带着人世间的情欲与道德的纠缠,有对世俗偏见的嘲讽与不甘,甚至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执着。那些离奇的遭遇,那些人鬼情未了的结局,读来让人脊背发凉,又让人唏嘘不已。那“好听”,是诡谲的乐章,是人性的变奏,它拨动你心底最隐秘的弦,让你重新审视这个世界,以及那些被忽略、被压抑的情感。
鲁迅先生推崇的书籍,往往带着一股子批判的锋芒。他的阅读,从来不是为了附庸风雅,更不是为了消遣。他读进去的,是社会的病灶,是时代的症结,是民族的苦难。所以他推荐的书,必然也是有着这种穿透力和解剖力的。比如,他对中国古典小说、诗歌的独到见解,对某些世俗文学的鞭辟入里的分析。他眼中的“好书”,绝非那种迎合大众口味、甜腻俗套的“小确幸”,而是能让人猛然惊醒,心生警惕的作品。它们可能让人读得不舒服,不痛快,甚至有点“扎心”,可正是在这份“不舒服”里,你才能触摸到真实,获得真正的力量。
所以,“好听”于鲁迅,有着更深层的意义。它不是表面的悦耳,而是内心的共鸣,是思想的激荡。它可能是《野草》中那些晦涩却力量万钧的低语,每一句都像一把尖刀,直插进你最不敢触碰的地方,让你在疼痛中思考,在迷茫中探寻。它也可能是他翻译的那些被压迫者的悲歌,让你听见那些微弱却不屈的声音,感受到人类共通的命运。
我记得初读《呐喊》时,那种憋闷、那种沉重,真不是什么“好听”的体验。闰土的麻木,孔乙己的悲凉,阿Q的愚昧,字字句句都像块石头,压得我喘不过气。可读完后,心里像是被重锤敲过,嗡嗡作响,久久不能平息。那不就是另一种“好听”吗?一种痛彻心扉的、却又让人清醒的“好听”。它让你听见民族的沉疴之音,听见底层人民的无声哭泣,听见那一代知识分子绝望而又坚韧的呐喊。这种“好听”,带着时代的风雷,裹挟着历史的尘埃,它让你无法逃避,必须面对。
鲁迅先生推荐的书,它们所发出的“声音”,往往是深沉的,甚至带着血和泪的腥味。但正是这种真切,这种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,使得这些作品拥有了穿越时空的魅力。它们不是轻歌曼舞的伴奏,而是号角与战鼓,是警世的箴言,是唤醒沉睡灵魂的雷鸣。它们会让你灵魂震颤,思想激荡,甚至会让你在某个深夜里泪流满面。但正是这些,让你从麻木中惊醒,从混沌中清明,从平庸中拔节。
所以,如果你问我,鲁迅推荐哪些书“好听”?我会说,那些能让你撕开表象,看清本质的;那些能让你心头一震,久久难忘的;那些能让你在痛苦中领悟,在思索中前行的——便是他心中真正“好听”的书。它们不追求表面的和谐与温情,却在深处蕴藏着震撼人心的力量,那力量如同旷野的风声,穿透一切,直抵肺腑,让人受益无穷,一生受用。这便是鲁迅式“好听”的独特魅力,一种超越了耳朵,直抵心魄的精神回响。
本文由用户 大王 上传分享,若内容存在侵权,请联系我们(点这里联系)处理。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://www.365yunshebao.com/book/685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