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问我,绝望的时候读什么书?问得好,也问得糟。
抱歉,我推荐的书,一本都做不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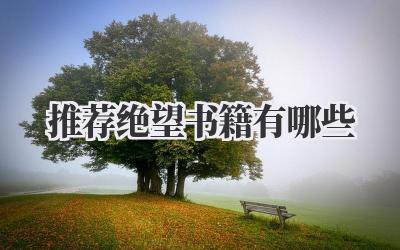
我给你指的路,不是向上的梯子,而是向下的台阶。它们不会递给你一碗温热的鸡汤,告诉你“人间值得”。它们只会递给你一把冰冷的手术刀,说,看,这就是你的病灶,这就是世界的真相,腐烂,空洞,且毫无道理。然后,在你凝视深渊,深渊也回望你的时候,你会奇异地发现一种平静。一种“原来如此”的,踏实的,落地的感觉。
因为最大的绝望,不是痛苦本身,而是当你痛苦时,全世界都在告诉你,你不该痛苦,你应该积极,你应该向上。而这些书,它们是你的同谋,是你沉默的病友,它们会坐在你床边,什么也不说,但你知道,它懂。它完全、彻底、毫无保留地懂。
所以,如果你准备好了,我们就开始这场“以毒攻毒”的阅读之旅。
第一站,是所有伪装者的地狱镜像:《人间失格》
太宰治。这三个字本身就带着一股潮湿的、挥之不去的霉味。
你是不是也这样?在人群中扮演一个小丑,用滑稽和讨好来掩饰内心深入骨髓的恐惧和疏离。你费尽心机,维持着一张“正常人”的面具,可面具下的那张脸,早已被冷汗浸泡得浮肿、溃烂。你笑着,可你的灵魂在尖叫。
那就去读《人间失格》吧。读叶藏。
这本书不是一个故事,它是一面镜子,一面哈哈镜,把你的所有不堪、懦弱、恐惧、自我厌恶,照得一清二楚,并且无限放大。叶藏的每一次“求爱”,每一次“搞笑”,每一次“沉沦”,都像是在你心上精准地扎针。你会感到一种被扒光的羞耻,一种被看穿的恐慌。你会发现,你引以为傲的“演技”,在太宰治的笔下,不过是小孩子玩泥巴一样拙劣的把戏。
读这本书的过程是窒息的。像被人用湿毛巾捂住口鼻,你越挣扎,那股绝望的气息就越浓。但读完,当你合上书,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时,你会感到一种诡异的松弛。因为叶藏替你走到了尽头,替你喊出了那句你不敢承认的判词:“生而为人,我很抱歉。”
他替你失去了做人的资格。于是,你,这个还在世间挣扎的幸存者,反而获得了一种喘息的许可。你终于可以不必再假装自己是个“合格”的人了。
第二站,献给那些感觉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灵魂:《局外人》
如果说《人间失-格》的绝望是向内的,是一种自我消耗的、湿漉漉的痛苦。那么加缪的《局外人》,则是一种向外的,干燥的、冷硬的荒诞。
你有没有那么一些瞬间?母亲去世了,你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,只是觉得天气很热。别人在高谈阔论生命的意义,你脑子里想的却是中午要吃什么。你遵守社会规则,不是因为认同,而是因为“大家都这么做”,图个省事。你看着周围人的喜怒哀乐,就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电影。
你觉得自己是个怪物。是个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。
去见见默尔索吧。
他就是你。他因为“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哭”,最终被判了死刑。这个世界审判他的,不是他杀人的行为,而是他没有“按规定”去感受和表达。他是个局外人,一个诚实地面对内心虚无,却被整个虚伪世界所不容的局地外人。
读《局外人》的感觉,就像在盛夏正午的海滩上行走,阳光猛烈,晃得人睁不开眼,一切都清晰得过分,却又显得那么不真实。那著名的开头,“今天,妈妈死了。也许是昨天,我不知道。” 冷得像冰。这本书会剥离掉你身上所有多余的情感赘述,让你直面一个核心:世界是荒谬的,生命是无意义的,而你试图从中寻找意义的行为,本身就是最荒谬的一部分。
当默尔索在临刑前,面对神父,喊出他对这个“温柔的、冷漠的世界”敞开胸膛时,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。是的,去他妈的意义。我感觉不到,我就是感觉不到。我拒绝表演。这份坦然,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它让你不再为自己的“格格不入”而内疚。
第三站,当你觉得自己的苦难已是极限时,请看:《活着》
前面两本书,谈的还是精神层面的困境。而余华的《活着》,则是把“苦难”这两个字,实体化,具象化,像一座山一样,直接砸到你脸上。
你失恋了?你失业了?你觉得人生无望了?
去看看福贵吧。
看看他是怎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,一个一个,以各种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方式离开他。妻子、儿子、女儿、女婿、外孙……命运像一个残忍的、没有感情的农夫,一遍又一遍地收割他生命里的一切。到最后,只剩下一头也叫“福贵”的老牛陪着他。
这本书的语言,冷静、克制,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残忍。余华不给你任何煽情的机会,他不给你留一点点哭的余地。他只是陈述。像一份法医报告,冷静地记录着一具尸体上所有的伤口。你读着读着,会发现自己的绝望是多么的“奢侈”,多么的“小布尔乔亚”。你的那些情绪内耗,在福贵纯粹的、物理性的、无法逃避的苦难面前,显得轻飘飘的。
《活着》不会治愈你。它只会告诉你,苦难是人生的底色,活着本身,就是一场漫长的、徒劳的挣扎。福贵的故事,不是为了让你“比惨”之后获得安慰。恰恰相反,它是为了彻底摧毁你对生活抱有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它把“活着”这件事,剥到只剩下最核心的内核——就是活着,不为什么,没有目的,没有回报。
当你被这本书碾压过后,你会发现,你所面临的困境,也许并没有那么面目可憎了。你能呼吸,能吃饭,能睡觉,这本身,就已经是一种近乎顽强的胜利。
如果以上还不够,这里还有两位重量级选手:
《斯通纳》—— 约翰·威廉斯。这本书献给所有在平庸中溺水的人。它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悲剧,而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绝望。一个大学老师,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,也没取得什么了不起的成就。爱错了人,干着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,人生就这么过去了。这本书的恐怖之处在于,它太过真实,真实到你能在斯通纳身上看到无数个自己。它告诉你,人生最大的悲剧,可能不是失败,而是你从未真正为自己活过。
《生于不幸》—— 齐奥朗。这位罗马尼亚的哲学“毒师”,是绝望的终极形态。这本书不是小说,是警句和箴言的集合。每一句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,精准地刺向你对生命、存在、希望的任何一丝幻想。读他的文字,就像在舔一块电池,会给你带来一阵阵触电般的、痛苦的清醒。他把悲观主义写成了诗。当你觉得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你的虚无感时,去读齐奥朗。他已经替你把一切都说尽了,而且说得比你所能想象的,更深刻,更优美。
这些书,它们不是药。它们是病理切片。
它们不会告诉你如何爬出深井,它们只会陪你一起,坐在井底,告诉你这口井的结构、深度和井壁上每一块苔藓的纹路。
奇怪的是,当你彻底了解了你所在的黑暗,承认了这片黑暗,甚至开始欣赏这黑暗的形态时,你反而不再那么害怕了。你触底了。脚下是坚实的土地,再也不会下坠了。
然后呢?然后,就没有然后了。读它。就对了。
本文由用户 好好学习 上传分享,若内容存在侵权,请联系我们(点这里联系)处理。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://www.365yunshebao.com/book/6492.html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