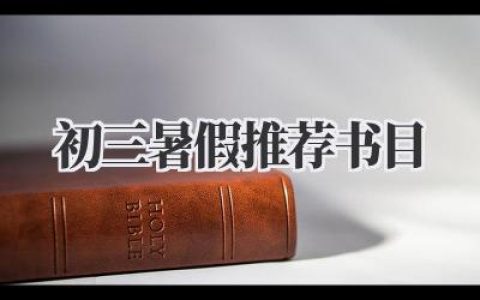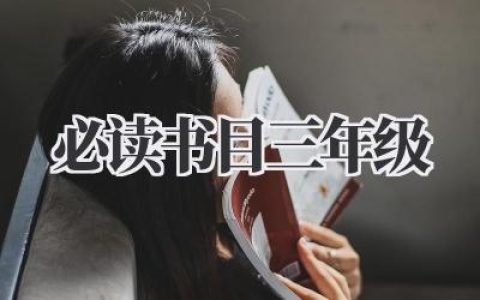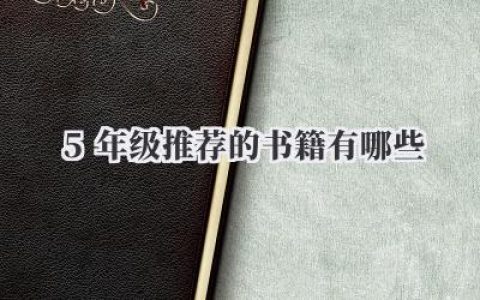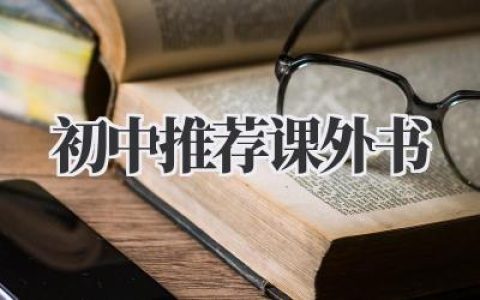聊这个,我不想给你拉一个长长的书单。书单是最偷懒的办法,也是最无效的。你看着单子去买,可能买回来一本垫桌脚都嫌它硌得慌的书。我想聊的,是几种能把你“拽进去”的体验,能让你读完之后,感觉自己身体里某个零件被替换掉了的体验。能给你这种体验的书,在我这儿,就叫文学。
第一种:抡起大锤,砸碎你世界观的
有些书,它不是来跟你交朋友的,它是来给你当头一棒的。它不负责治愈,只负责让你看见世界的裂缝,看见人性的深渊,甚至让你怀疑自己。这种书,读的过程通常不怎么愉快,甚至可以说痛苦。但读完之后,你再看这个世界,眼神就不一样了。

首当其冲的,必须是卡夫卡。对,就是那个写《变形记》的。你一觉醒来,变成了甲虫。这设定荒诞吗?简直荒诞到可笑。但你读下去,那种被家庭、被社会、被整个世界排挤、抛弃、视为异类的窒息感,会像潮水一样把你淹没。你不再是读者,你就是那只甲虫,在自己的房间里无助地挥舞着细小的腿。卡夫卡写的不是一个故事,他写的是一种现代人的普遍困境——存在的荒谬与孤独。他的书,就是一把锤子,砸开我们用日常生活琐事堆砌起来的坚冰,让你看到冰面下那又冷又黑的深水。
同样的大锤,还有俄国人。陀思妥耶夫斯基,这家伙简直是个疯子,一个对人类灵魂进行残酷拷问的疯子。《罪与罚》里,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人之后那种心理的煎熬、高烧般的呓语、在街上游魂似的晃荡……陀翁的文字有一种病态的魔力,黏稠、滚烫,充满了汗水和铁锈的味道。他把你按在那个穷困潦倒的大学生身体里,让你跟着他一起发疯,一起恐惧,一起面对良心的审判。读他的书,你会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放在火上烤。烤完之后,你对善与恶、罪与罚、上帝与虚无的理解,会被彻底颠覆。
这类书,不甜,甚至很苦。但它能强行拓宽你生命的维度。
第二种:像水银一样,无声无息渗透你的
跟上面那种大开大合的相反,有些书,它不动声色。它就像春雨,润物细无声;也像水银,钻进你每一个毛孔,等你发觉时,已经中了毒。它们不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只写一些日常的、纤细的、甚至有点病态的美。
我第一个想到的,是川端康成。他的《雪国》,你把它当爱情小说看?那就太小看它了。驹子这个人物,她身上的那种徒劳的美,那种生命力与虚无感的交织,才是最动人的。那句“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,便是雪国”,简直像一句咒语。火车窗玻璃上,叶子姑娘的脸和窗外的暮景重叠在一起,那种虚幻的美,美得让你心口一紧。川端康成的文字是“冷”的,带着一种日本物哀文化特有的、对“美之将逝”的迷恋和感伤。他不会告诉你什么大道理,他只是把一种极致的美,一种带着毁灭气息的美,摆在你面前。你看过了,就再也忘不掉。
还有加拿大的爱丽丝·门罗。她一辈子都在写短篇小说,写的都是加拿大某个小镇上普通女人的生活。没有离奇的情节,没有戏剧性的冲突,就是婚姻、出轨、衰老、回忆……这些再寻常不过的碎片。但门罗的厉害之处在于,她能把时间的褶皱给你抚平了再揉乱,让你看到一个人漫长一生里,某个瞬间是如何决定了她后来的全部命运。她的叙事,像剥洋葱,一层一层,剥到最后,让你眼眶一热。你读到的不是故事,是时间的重量和人生的无奈。那种后劲儿,比喝烈酒还大。
这类书,它不改变你的世界观,它改变你的“体感”,让你对美、对时间、对日常生活的感知,变得更敏锐、更细腻。
第三篇:一面镜子,照出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鬼样子
还有一种书,它就是一面让你无处遁形的魔镜。你读的不是别人的故事,你是在跟自己对质。你一边读一边骂:“这主角怎么这么矫情/懦弱/混蛋?” 然后,一个冷不丁的瞬间,你发现,你骂的其实是你自己。
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就是这样一本书。多少人年轻时读它,都觉得自己就是霍尔顿,觉得全世界都是“假模假式”的傻逼,只有自己最清醒、最纯粹。那种少年时代的迷茫、孤独、对成人世界的愤怒和不屑,被塞林格写得入木三分。可等你年纪大了再读,你可能会觉得霍-尔顿这小子真够烦人的。但同时,你心里某个角落会被刺痛——你是不是也曾像他一样尖锐过?你现在,是不是也活成了自己当年最讨厌的那种“假模假式”的大人?这本书,就是青春的墓志铭,也是一面照妖镜。
国内作家里,余华早期的作品,特别是《活着》,也有这种力量。福贵的一生,被命运反复碾压,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,最后只剩下一头也叫“福贵”的老牛。这个故事,惨吗?惨绝人寰。但余华的牛逼之处在于,他用一种极其冷静、甚至有点冷酷的语调来讲述这种惨。你读的时候,不会嚎啕大哭,但那种巨大的悲伤和无力感,会像石头一样压在你胸口,好几天都缓不过来。它让你思考的不是别的,就是“活着”这件事本身。当所有的意义、希望、财富、亲情都被剥夺后,人为什么还要活着?这本书不给你答案,它只是把这种赤裸裸的、坚韧得近乎残忍的生命力甩在你脸上。你合上书,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,会突然对“活着”这个词,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。
第四种:语言的魔术,让你沉迷于文字本身
最后一种,可能有点“门槛”。这类书,故事退居其次,甚至没有故事。你读它,纯粹是享受作者玩弄文字的快感。他像个魔术师,把一个个普通的方块字,组合成了让你眼花缭乱的奇观。
博尔赫斯必须拥有姓名。这个阿根廷的失明图书馆馆长,他写迷宫,写镜子,写一个虚构的百科全书,写一个能记住一切的人。他的小说,短小精悍,却像一个精密的宇宙模型。你读他,不是在看故事,是在做一场智力游戏,一场思想实验。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密度,指向无穷的可能性。读博尔赫斯,会让你对“小说”这种体裁的认知被彻底刷新,原来文字可以这么玩!
当然,还有写《洛丽塔》的纳博科夫。抛开那惊世骇俗的题材不谈,纳博科夫的英语,华丽、精准、充满了音乐感和双关语的机锋,简直是语言的盛宴。他能用最美的文字,去描绘最病态的情感,这种张力本身就构成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性。
回到中文世界,我很喜欢汪曾祺。他的文字,跟博尔赫斯、纳博科夫完全是两个路子。他不华丽,他“淡”。但那种淡,是把所有的味道都炖进去了的淡。他写吃的,写草木,写旧时候的那些人那些事,寥寥几笔,活色生香。读他的散文,就像在冬天的午后,喝一碗热腾腾的汤,从胃里一直暖到心里。那种对生活的热爱,那种从平淡日常中发现诗意的能力,藏在他朴素的文字背后。他的书,教你如何用审美的眼光,去观察这个世界。
所以,到底哪些属于文学书籍?
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。对我来说,能让你读完后,或沉默,或激动,或怅然若失;能让你暂时忘记刷手机,忘记KPI,忘记今晚吃什么;能让你在合上书之后,重新打量这个熟悉的世界,并发现一丝陌生的光亮的书……
它就是。
去找吧,别信任何人的书单,包括我的。去书店里闻闻油墨香,去图书馆的角落里蒙着灰的书架上翻一翻,去找那本能跟你“通上电”的书。找到那本让你半夜睡不着,非要跟人聊聊的书,那它对你来说,就是最好的文学。
本文由用户 大王 上传分享,若内容存在侵权,请联系我们(点这里联系)处理。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://www.365yunshebao.com/book/6564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