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问“看”什么书,而是“听”什么书。一字之差,天壤之别。对于我们这种靠码字、靠结构、靠在脑子里搭建场景和人物关系为生的人来说,耳朵,有时候比眼睛更重要。眼睛看字,看到的是符号;耳朵听书,听到的是活生生的人,是流动的节奏,是藏在字里行间的呼吸和心跳。
所以,我推荐的“好听”的书,标准有点怪。不只是故事好,更重要的是,它能在你的耳蜗里“演”起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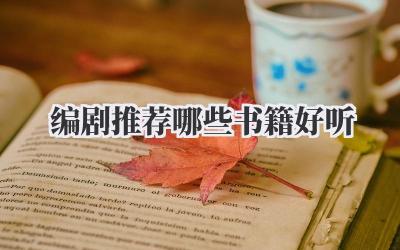
首当其冲,我强烈建议所有想写对话、或者觉得自个儿对话干瘪的同行,去听王朔。
别看书,去听。找个好版本,最好是那种京片子味儿够足的演播者。你听《动物凶猛》,听《顽主》,听《一半是火焰,一半是海水》。你听的不是一个故事,是那个年代北京胡同里、饭局上、出租车里弥漫的那股子空气,那种混不吝的、带着自嘲又有点形而上的贫劲儿。王朔的语言,是自带BGM和表演节奏的。他的每一个停顿、每一个“操”、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俚语,都是人物性格和情绪的精准外化。这种语感,光看文字,体会不到十成。你得听,让那些句子像小鞭子一样抽打你的听觉神经,你才能明白,哦,原来对话可以这么写,可以这么“不着调”,但又这么精准地戳在人物的骨头缝儿里。
听他的书,就像上了一堂顶级的台词课,教你的不是怎么写出“正确”的对话,而是怎么写出“活”的对话。
如果说王朔是外放的、张扬的,那另一个极端,你得去听刘震云。
听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这本书,光看,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绕,有点絮叨。但是你听进去,那完全是两码事。刘震云的厉害之处在于,他把中国最底层老百姓那种“转弯抹角”的说话方式、那种藏在无数废话之下的真实意图,给你原生态地呈现了出来。书里的人物,为了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,跋山涉水。你听着那些“俺”“恁”,听着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家长里短,你会突然在一个瞬间,脊背发凉。你会听懂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。他的对话里,有大量的潜台词,有无数的言外之意。这对于编剧来说,是宝藏。我们天天琢磨怎么让角色“话里有话”,刘震云直接把生活的褶皱烫平了给你看。听他的书,是磨练心性,是让你学会怎么从一堆朴素到掉渣的语言里,提炼出人物最核心的动机和困境。
说完语言,再说说结构。
想感受什么叫宏大叙事、什么叫草蛇灰线、什么叫叙事的野心,去听《三体》全集。我知道,这书你看过八百遍了。但你听听广播剧版,那种带音效和不同角色配音的版本。这不是单纯的听书,这是在听一个“声音的电影”。抛开科幻的外壳,你作为一个编剧去听,要去捕捉它的信息密度和节奏。刘慈欣是怎么在第一部里埋下伏笔,然后在第二、第三部里让它石破天惊地炸开的?他是怎么处理大段的物理学理论,让它不那么枯燥,甚至产生一种史诗般的美感的?闭上眼睛听,你的大脑会被迫自己去构建画面,去填充细节。这个过程,本身就是一种绝佳的思维训练。你会更清晰地感知到故事的骨架,而不是被文字的细节所迷惑。听完一遍,你脑子里对“史诗感”和“世界观构建”的理解,绝对能上一个台阶。
如果《三体》是宏伟大厦,那想学精巧的迷宫,你得听东野圭吾,尤其是《白夜行》。
这本书的妙处在于它的“全知”叙事,却又对主角的内心世界只字不提。你作为一个读者,像一个幽灵,飘在所有人物身边,看着他们因为雪穗和亮司这两个黑洞般的存在,命运被一个个搅得粉碎。听书,这种感觉会加倍。因为没有文字的视觉引导,你只能靠声音去拼凑线索。演播者冷静克制的语调,配上故事里一件件冰冷的事件,那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悬疑感会把你牢牢抓住。这对编身处其中的我们来说,是学习如何用侧写和侧面事件来塑造核心人物的绝佳范本。主角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内心独白,但他们的形象却比谁都深刻。这功夫,值得我们偷一辈子。
最后,我想说点不一样的。去听点非虚构。
没错,听历史,听人物传记,甚至听一些高质量的真实罪案播客。
为什么?因为生活,永远是最高明、最大胆的编剧。你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人物弧光,可能还没有《曾国藩传》里,一个中年油腻官僚在无数次挣扎和自我唾弃后,最终“脱胎换骨”的过程来得震撼。你费尽心机设计的反转,可能还没有真实历史事件里,一个微小细节引发的蝴蝶效应来得巧妙。
去听听那些真实的人生。听他们怎么说话,怎么做决定,怎么在时代的洪流里被裹挟、又怎么试图反抗。这些声音,是最原始的素材库。它能让你的人物不再是悬浮的、靠“设定”堆砌起来的纸片人,而是有根的,是从真实的人性土壤里长出来的。你会发现,最离奇的戏剧冲突,最复杂的人性纠葛,剧本都写好了,就在那些真实的故事里,等着你去挖掘。
所以,别只盯着编剧理论和拉片了。关掉屏幕,戴上耳机,把耳朵当成探针,伸进这些“好听”的书里去。在那里,有语言的韵律,有结构的骨架,有人物的灵魂,还有生活本身粗粝而滚烫的呼吸。
这比你看一百本“如何写作”的书,管用得多。
本文由用户 好好学习 上传分享,若内容存在侵权,请联系我们(点这里联系)处理。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://www.365yunshebao.com/book/6970.html

